文/陳鈺雯
■ 林宛瑄:來回於海洋與島嶼的「兩棲視角」
銜接張君玫的下一場,林宛瑄教授舉了《航海王》(ONE PIECE)中的經典片段。點出人類感官的局限,角色之一的哥爾.D.羅傑有聽到萬物的能力,石頭告訴他「生命之聲」,這是很多人類都聽不到。人類藉由數位科技捕捉訊息,有些人眼睛看不到、但耳朵敏銳。《航海王》中的「惡魔果實」,這物幫助人們發展某種潛力,以人的身體為基礎看世界。
林宛瑄開場指出,這場講題是根據《航海王》的世界觀,在「嶼之宇」子題框架中發想,解釋現象可能連結的概念理論,展演如何取徑理論、激發想像。她借鏡「兩棲人類學」與「宇宙政治」,討論《ONE PIECE》中由島嶼航行開展出的政治與倫理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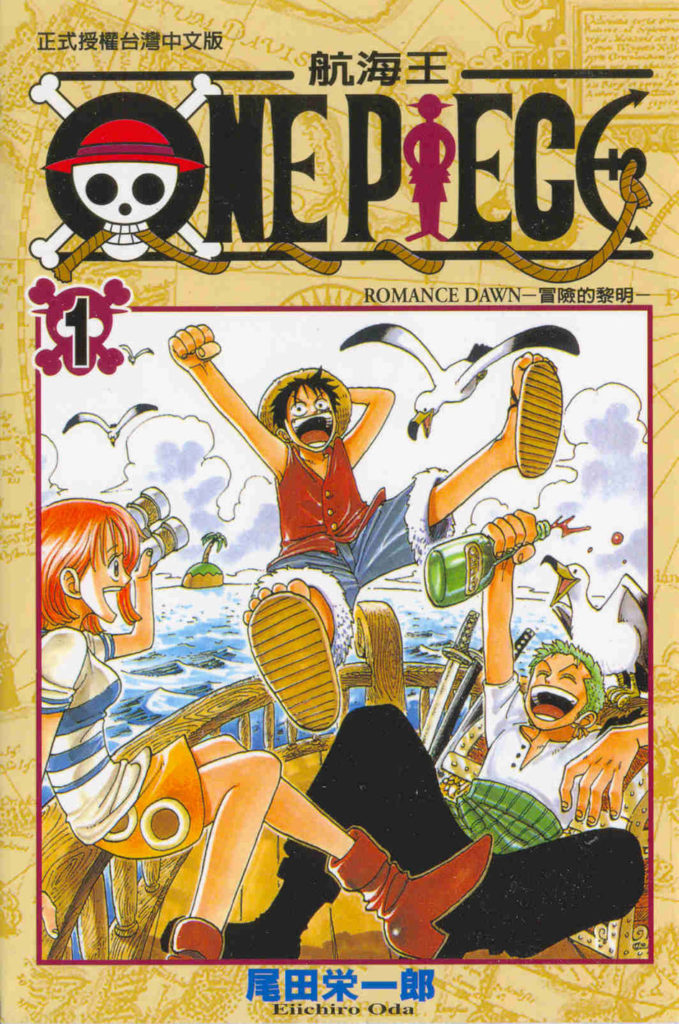
《ONE PIECE》地理空間中,海洋面積遠大於陸地面積,海上分布著許多島嶼。哥爾.D.羅傑是這個世界觀裡最受人景仰的海賊王,不但完成航道的偉大之舉,還留下遺言鼓勵大家湧向大海。然而,海賊王追求自由,是世界政府的眼中釘。總部位於紅土大陸的世界政府高舉正義大旗,最高決策集中少數人手上,刻意造成各大海洋難以交流的狀態,讓各地區因無知與恐懼,而屈服於世界政府轄下。成為海賊,相當於衝撞既有體制,顛覆世界政府說了算的常識。海賊行動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並體現了來回於海洋與島嶼之間的「兩棲視角」。
成為海賊,相當於衝撞既有體制,顛覆世界政府說了算的常識。海賊行動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並體現了來回於海洋與島嶼之間的「兩棲視角」。
林宛瑄介紹到故事中索隆的原型人物,是名字取自坂本龍馬的霜月龍馬,來自新世界中長期鎖國的和之國。和之國大名光月御田如同坂本龍馬,認知到日本只是一個海嶼,對船隻深感興趣,對於沒有見過的世界充滿驚喜。御田投身遼闊海洋與登上島嶼時的喜悅之情,呼應《ONE PIECE》中許多角色的心情。
對他們而言,海洋也象徵友情的連結, 通往出身地以外的地方。陌生的島嶼,則顛覆了既有的知識結構,應許了不受單一觀點限制、實現自由正義的寬廣可能性。因此世界政府與海賊之間的抗衡,可說是陸地思維與海洋思維的衝撞。世界政府奠基於陸地本位主義,將空間定位為固化後的領域,承載僵化的權力結構,掩蓋關係形成與變動的過程和可能性,讓天龍人永遠是天龍人,奴隸永遠是奴隸。
陌生的島嶼,則顛覆了既有的知識結構,應許了不受單一觀點限制、實現自由正義的寬廣可能性。世界政府與海賊之間的抗衡,可說是陸地思維與海洋思維的衝撞。
■ 探索在我們之中的海洋
海賊們出海讓關係重新開始流動的行動,體現了藍海人文主義與群島化思維的「去陸地中心」 思考。去陸地中心思考,將海洋與島嶼重新設想為關鍵空間,探討由此開展的空間、歷史、群體等想像以及理論可能。探遊「在我們之中的海洋」,把海洋視為島嶼的海洋,並與島嶼共思,那麼我們將能看見島嶼如何持續相互生成,看見海洋如何形塑我們的系譜,感覺與身體的想像等等。
林宛瑄準備的圖片展示了群島思維,即拋棄二元世界觀,透過島嶼相互建構,在島嶼運動的連結中促合。隨著故事角色尋找空白的百年歷史,試圖發現世界政府掩蓋的真相,冥王雷利的智慧箴言,指向內在於島嶼運動中的知識與思考生成歷程。
《ONE PIECE》的角色們各自在航行遍歷島群時,逐步摸索形成觀點,得出關於重新聚合、生成新世界的「特異答案」。
然而將島嶼視為新天地開展之路徑的同時,我們需留心其間是否偷渡了西方陸地本位想像,過度浪漫化熱帶島嶼的「神祕吸引力」,導致循線歸結到「陸與非陸」的二元思維。若我們將陸地與海洋各自視為流變之物,而不是「陸與非陸」,就可以看出島嶼的形成過程,涉及陸地與海洋等差異狀態的轉變過程,本身就是充滿複雜張力的過程。
林宛瑄介紹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說法,大陸型島嶼與海洋型島嶼都是水與土等元素之間相互碰撞共同流變而成的差異經驗。而從神話角度來看,將人們吸引到島嶼上再創造新生活的衝力,延續的是產生島嶼所需的雙重運動,雖然歷史上較常見的是像魯賓遜這樣,把陸地生活搬到島上,因而無法創新生活樣態的例子。

■ 人類是本體論上的兩棲類
島嶼揭示的元素衝突與雙重運動,可以進一步連結到兩棲人類學。林宛瑄援引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哲學語言,說明人類是遷移不定的生物,渴望轉換不同元素前往他方,不會堅守單一元素環境,因此人類可說是本體論上的兩棲類。斯洛特戴克主張海德格等哲學家只著眼於聚焦土與火元素的「乾哲學」,既然人類是可以居住於至少兩種以上環境的兩棲生物,時時面臨要選擇空氣還是水的問題,那麼哲學也不該乾濕分離,我們且應該探討與乾溼不分離環境相應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關係。
人類是遷移不定的生物,渴望轉換不同元素前往他方,不會堅守單一元素環境,因此人類可說是本體論上的兩棲類。
林宛瑄接下來談及博思(Rene ten Bos)延伸斯洛特戴克對水元素的討論,從「沉潛(diving)、島嶼與橋接(bridging)三個相互關聯的主題」來探討兩棲人類學的理論潛力與體現。
其中,沉潛泛指任何從對峙存在模式轉換到浸泡存在模式(medial way of bing)的作為。主體在此與在彼的世間客體相對的想像,即是對峙模式最佳例證,浸泡模式則是一種「我消溶於球體(sphere)之中」的存在模式。球體指向了斯洛特戴克著名的免疫球體理論,簡言之,免疫球體是一種發揮著免疫系統作用的空間,為了受外域影響的存在,涵蓋內部也對外顯露。浸泡於球體之中涉及的是「in」和「with」的生存樣態,可被理解為「某物與某物共在於某物之中」,尤其是共在於水元素中,一起被環繞、被流經。但人類作為兩棲生物,還是會浮出水面呼吸空氣。人類在兩元素中拉鋸,沉潛入水肯定的是對「接觸、參與、涉入」的期待,離水呼吸空氣時則帶出批判的距離,兩者都是人類學不可忽視的面向。
人類在兩元素中拉鋸,沉潛入水肯定的是對「接觸、參與、涉入」的期待,離水呼吸空氣時則帶出批判的距離。
此外,羊水是母體內部的海洋,曾在子宮中被羊水包覆的人,乃是誕生於水中,因此渴望被各種微球體與巨球體包覆環繞。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島嶼,斯洛特戴克認為人類需要藏匿在島嶼中,保護自己免受外在世界的威脅,因為人類不可能吸納得完所有的威脅。而且人類不僅是在環繞的海洋中偶遇島嶼,還會主動建造島嶼。環繞人類的海洋像是一種隔離裝置,並創造了自身的島嶼。
人會造島同時也會跳島,對曾經引領陸棲全球化的繪圖師與海員來說,出海是一種對陸棲生活的抵抗。若從航海視角來理解資本社會,流動且具有風險的海洋,正是與工業向外拓展運動相應的元素,海洋也能連結遙遠的兩地,以利商業與文化交流。在我們的三次元世界中,總是向外尋求機會的創業家是典型的跳島者,但連結兩地的造橋者,與不停漂移的探險家也是跳島者。
■ 跳島者與造島者
跳島者與造島者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兩者可能相互轉換。兩棲人類學突顯了水與土相互碰撞而生的差異經驗之複雜性,兩棲族群的觀點與對世界的想像也並未定於一尊,那麼想法不同的種族們要如何共存呢?
林宛瑄話鋒來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與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的差別。拉圖爾(Bruno Latour)認為世界主義奠基於單一自然論(mononaturalism),相信西方理性及科學的力量能夠通曉唯一的宇宙,人類可以在其中建立一個所有人都樂於當公民的世界都會。世界主義將政治置於給定的一統框架之下,人們所要做的就是擺脫對主觀看法的附著,就可以進入普同世界,戰爭都能夠獲得仲裁,和平也將得以實現。拉圖爾認為並非如此,世界本身並非單數,並不存在一個可以仲裁衝突的單一自然/普同世界,也沒有奠基於單一給定世界的世界政治可言。
21世紀是大一統環球迸裂後的全球泡沫(global foam)時代,社會由微小球體群集而成,每個泡沫都是有著內部環境的單子。
延續對免疫球體的討論,斯洛特戴克同樣認為,21世紀是大一統環球迸裂後的全球泡沫(global foam)時代,社會由微小球體群集而成,每個泡沫都是有著內部環境的單子,但彼此以薄膜互生相接,任何一個泡沫的消長都會牽動相鄰泡沫與泡沫整體。但斯洛特戴克似乎認為,全球是一個有限的概念,也因此全球泡沫會日益密實到難以行動的程度。
拉圖爾則認為我們並非只有一個陸棲全球,全球泡沫應該是非人增生後的開闊想像。我們需要一種慢慢組構而成的宇宙政治,重新想像如何安排人類的居所,同時對以主體再現客體的方式區分「人與非人」的做法加以置疑,重新探索我們如何不依靠給定的單一世界觀組構世界,要組構怎樣的世界,與哪些人與非人「竭盡全力地」共組世界。
這些「人與非人」不是主客體再現邏輯的產物,因此是「新人與新非人」。莫琳(Marie-Eve Morin)強調,宇宙政治的內在性組構工程包括涵納那些我們認為「落後、愚昧、不理性、不夠進步的聲音」。以進不進步作為判準的政治想像,其實可能與西方殖民者對落後種族的教化邏輯類似。
Morin認為我們應該重新認知,我們心目中的怪物,例如恐怖份子,是不會消失的。我們甚至要與怪物共居,思考如何在「不排除任何相互衝突的主張、利益與情感的前提下」,共同生存下去。屆時我們也可能會發現,怪物其實不是怪物。

